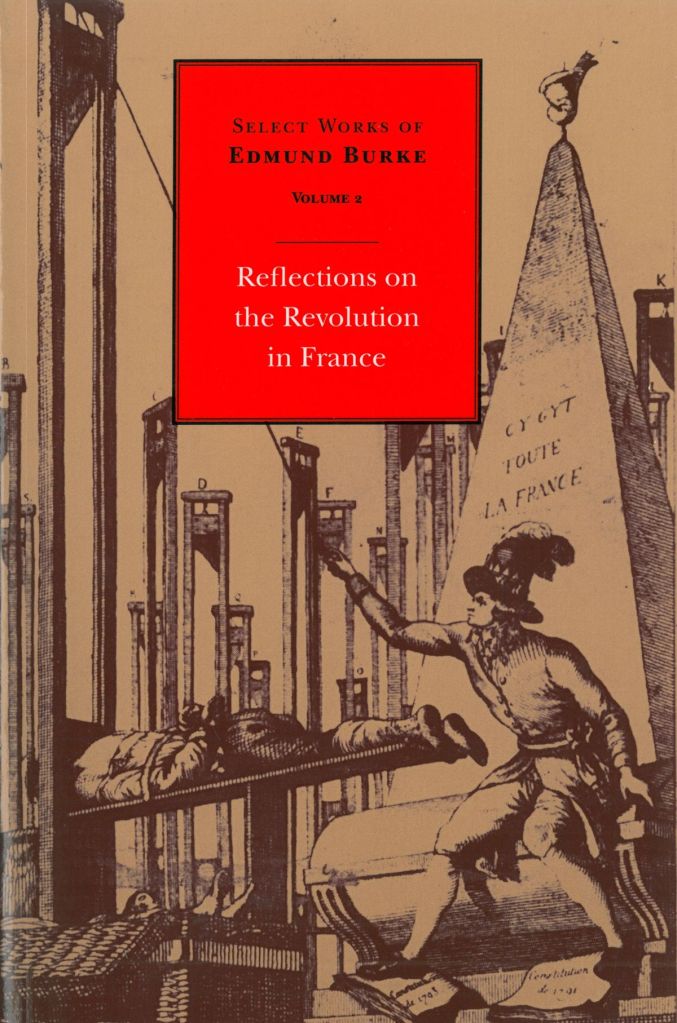你們覺得你們是以這種方式與偏見鬥爭,但實際上你們是在與自然開戰。
埃德蒙・伯克《法國大革命反思錄》,頁84
對於法國大革命催生的一切「新事物」都應該毫無保留地肯定與接受嗎?在1790年的愛爾蘭裔英國政治家、哲學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1729-1797)眼中,法國大革命連同它的種種後果並不值得人們像一些英國意見領袖那樣魯莽地對其表達欣然的恭賀;大革命毋寧是一場對於人類文明與歷史影響深遠的災劫,反而亟待當時已暗含了將革命風潮帶到本土的許多條件的英國社會深切反省、引以為戒,應倡導有識之士協力杜絕大革命的火焰蔓延至英倫境內。對於早年曾熱烈支持美國獨立戰爭,長期反對英國王室特權,當時已屆遲暮之年並積累著終生政治經驗於一身的伯克而言,迫使他做出對法國大革命如此負面判斷的理由,顯然不是敵對者扣在他身上的「反對變革」、「維護威權」的反革命帽子能夠解釋清楚的。
驅動伯克耗費時間、不吝筆墨寫下後來以《法國大革命反思錄》(1790)之名出版的長篇書信,其間向其法國友人、更是向英國人反復申述其核心觀點與明確立場而不顧行文可能在讀者看來過於繁複冗長的真正理由,在於作者心中所抱持的關於人類社會恆常運作的宏觀結構的知識,某種源遠流長、其來有自而並非新近創造的具備了審慎品質的智慧,令他在確認了法國大革命事實上的淺薄與拙劣之後,有許多公道、诚恳而不失批判鋒芒的話語實在不吐不快,哪怕這些話語最初必須以迂迴婉轉的修辭、重疊綿長的風格來表達,尤其當說話對象是那些尚無法擺脫革命理念的崇高光環的魅惑或者仍因為破壞了舊制度而被狂喜沖昏頭腦的人們的時候,這裡邊不盡是法國人,也包括不少英國人。
伯克政治思想的全部核心在於從歷史而不是理論出發來把握人類社會運作的結構,以至於他能夠洞見慣例、制度與傳統在社會運作中所起到的壓艙石般的穩定作用,因而總結出以下根本決斷:維護並逐步改革經過具體歷史條件檢證過的既有社會制度,要比僅僅基於抽象理論就主張隨手推翻既有社會制度、從頭開始試圖迅速創建出新社會制度的冒險做法更符合人類——包括了古人、今人及來者——的整體利益。正是基於這個根本決斷,伯克必須站在為法國大革命的發生感到歡欣鼓舞的人們的對立面,堅持以一種審慎的態度來逐一批判大革命的種種荒唐、魯莽的舉措:基於啟蒙思想家們未經歷史驗證的抽象的「人權」、「平等」、「自由」概念來確定革命理念與實踐原則,根據幾何學為國土規劃各級行政區域以及用算數(數人頭)的方法作出公意的決斷,委派原來位於底層行業的民眾、在財產上朝不保夕者和複雜政治活動的門外漢來擔當立法工作、組建國家治理機構,摧毀等級、秩序與人類類別的多樣性,非合理地殘暴對待王室和貴族,不尊崇習慣法和保障個人財產權,沒收教會的不動產為國家所有並用於抵消政府債務,不是根據每個群體佔有財產及對社會貢獻(如納稅)之多寡來確定該群體參與政治的權利,等等。在伯克看來,大革命實際上是為從低級政客、新興金融商人到政治文人及二流哲學家等種種狂熱野心家、投機牟利分子、鼠目寸光之輩提供了登台機會,儘管社會制度發生劇烈變革,不變的是人類對權力的爭奪與濫用,更從一開始就暗含了當政治實驗/豪賭失敗後勢必將專制主義從原有制度的限制中重新解放出來的深重危機,那才是對人權的真正損害(頁254)。
伯克對所謂的「啟蒙時代」始終抱有戒心,無法認同許多啟蒙思想家提出的新奇、時髦的理論,對於盧梭的思想尤為深惡痛絕。而他對這些思想的批駁則首要地集中於它們的通病即抽象特質之上。儘管伯克自己同樣熱愛自由,但他所擁護、所追求的自由絕不是啟蒙思想家口中的完全脫離了具體歷史環境的「自由」,他絕不會「以赤裸裸的、孤立的形而上學的抽象,剝離事物與其周圍事物的聯繫,簡單地稱讚或者是責備與人類行為和利益有關的任何事物」,這是因為「具體環境在現實中賦予了每一個政治原則以其自身的顯著色彩和獨特的作用。也是依據具體環境,才能知道每一個社會方案和政治設想對人類究竟是有益的還是有害的」(頁24-25)。同樣基於毫無根據的、實際上是違憲的抽象原則,在英國的大革命支持者,如讓伯克嗤之以鼻的理查德・普萊斯牧師,便開始鼓吹「普選」,主張不是由所有人民選舉出來的國王就是非法的國王,人民應該有權利選擇自己的統治者,可以因國王行為不端而罷黜國王,可以組建自己的政府(頁34-37)。伯克認為,這樣荒謬的理論,不過是對抽象自由的阿諛奉承而背離了英國政治的歷史環境和人們的具體自由,更是以向著民眾發出的模棱兩可、含糊其辭的魅惑謊言來損壞英國傳統制度的根基。以盧梭為代表的啟蒙思想家往往是以標新立異的言論達至震撼和吸引公眾的目的,企圖引發「在生活、風俗、個性以及特殊環境下能夠對政治和道德產生全新的、意想不到衝擊的奇跡」(頁235)。追逐在啟蒙思想家之後的二流哲學家、詭辯者則把最保守的理念樹立成主要敵人,將它與相對開明的聲音連同保守理念的錯誤之外可能存在的合理的部分通通捆綁起來給予猛烈攻擊,致使所有為傳統制度與正義原則辯護的事業都遭人厭惡(頁52),並以革命政治學為人民鍛煉出鐵石心腸。殊不知「同一種惡總會找到新的瓶子來裝舊酒」,當對歷史缺乏知識的人們以為在用新的旗號來與古老的邪惡誓死搏鬥的時候,同樣的邪惡,甚至是更大的邪惡,已經在醞釀當中了(頁200),說不定哪天就會反噬其身。
藉著反擊那些鼓吹抽象理論而企圖損害英國社會制度的大革命支持者,伯克反復重申了社會制度必須得到維護的基本原則,進而提出了變革社會制度的方法。在伯克的理論中暗含著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社會制度之所以應該得到維護,就在於這個制度是基於「以憲法的名義運行的社會約定和社會契約」而建立起來的,它的合法效力來源於「同一個權威——共同的約定和原始的社會契約,即國家的全體同意」。恰恰是根據這個先決條件,「從該契約中獲得重要利益的人,都有義務維護他們相互間的公共信任」,而無論是根據習慣法還是根據以習慣法精神所制定的成文法來訂立法律,「只要這些條款還被遵守、同一個政治共同體還在繼續,就對國王和人民具有同樣的拘束力」(頁45),因而不應該遭到無理而魯莽的隨意廢除。在此基本原則之下,必須維護社會制度與在特殊情況下做出偶爾背離和主動變通,兩者便不一定是完全不可調和的。至於變革社會制度的方法,則是僅僅改變不良的、必須背棄的部分,而不能從根本上企圖創造一個全新的社會秩序因而「導致整個公民以及政治群體的解體」。伯克寫道:「一個國家,如果沒有進行改變的方式,就等於沒有自我保全的方法」,然而,一個可以長久存續的政體在於從未毀掉整個建築物的構架,有能力在經歷動蕩的歷史事件後用沒有受損的部分更新舊組織中有缺陷的部分,並使得照原樣保留的舊的部分與更新了的部分相互適應(頁46)。伯克深刻地指出:「革新精神往往是自私秉性和偏狹觀念的產物。那些從來不去回顧他們祖先的人也不會去展望他們的後代」(頁61)。在明確保守與傳承的原則同時,不將改進原則排除在外而任其自然而然、無聲無息地完成,這就是英國人對於社會制度變革的審慎的智慧。而法國大革命所採取的徹底廢除和破壞傳統制度的專斷做法,恰恰顯示出革命者沒有與具體難題作鬥爭的能力與毅力(頁230-231),仿佛其社會制度「完全不配進行任何形式的改革」(頁187),任何與革命者持相反意見的人都成了早已遭到徹底抹黑的舊制度的幫兇(頁178)。既然斯巴達已經成為你的命運,那麼就為它增光吧。這句引自西塞羅的話成為伯克眼中一位正直的改革者所必須恆久堅持的規則。國家並非任人塗鴉的白紙,「真正的政治家所思考的往往是如何最充分地利用他國家現有的這些材料」,以之作為制度改革的基本條件(頁217-218)。
當社會制度建立起來,當它的恆常運行成為慣例,一些比制度本身更有價值的東西便產生出來,形成某種必須與制度交織在一起才能存在的獨特的協調關係與適應狀態,這是制度下的所有等級都賴以生存的核心利益之所在。因此,對於制度的破壞,所破壞的不僅是制度,更是這種難得建立起來的協調狀態。伯克認為,維護等級秩序和保障個人權益,這兩方面其實是相互耦合、不能彼此分離的,反而是力圖無差別地削平一切位於抽象平等水平以上部分的做法,才是不公正的、損害所有人利益的。「那些試圖消除差異的人,永遠都無法實現平等」(頁83)。事實上並不像革命者所宣稱的那樣,等級制度必然要與自由精神相互衝突,因為恭順中有驕傲,順從里有尊嚴,即便是本身處於奴役地位的人其心中依然可以鮮活地保留著崇高的自由精神。而一個文明社會中的貴族的崛起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是與該文明社會的肌理交織在一起的,伯克因此稱其為「自然貴族」。作為一個能合法主張其地位的階層,他們以高尚道德、淵博學識為社會提供普遍原則,較平民階層而言更適合引導社會的發展。只有當統治者、貴族、教士、軍隊、平民各等級都安守本分並且相互有機關聯、彼此促進的時候,所有人才能獲得最大利益。他對法國友人進言:倘若法國能夠遠離大革命的錯誤路徑,「你們就會有一部自由的憲法、一種強有力的君主制、一支訓練有素紀律嚴明的軍隊、一個開明而可敬的教士階層、一個謙和但意氣風發的貴族階層來引導你們的美德,而不是遮蓋它;你們會有一眾受保護的、知足的、勤勞而又恭順的人民,他們被教導著去尋找和認識不論在何種條件下,靠美德就能發現的幸福。人類真正的道德上的平等就在於此,而不是通過一個巨大的虛妄,激發那些命中註定就要一生卑微地跋涉在勞碌旅途上的人產生錯誤的想法和無望的期待,這種虛妄只能加劇和惡化永遠都無法消除的真正的不平等,而且公民生活秩序的建立是為了平等地保護那些只能生活在一種卑微狀態中的人的利益,以及那些雖然有能力去過更光彩奪目的生活,卻未必更幸福的人們的利益」(頁66)。恰恰在一個以這樣的原則建立起來社會制度下,「如果我們的自由一旦受到威脅,正如它經常面臨的那樣,它還能經受住種種特權的鬥爭風暴,得以保全」(頁50)。《法國大革命反思錄》出版三年後,法國進入恐怖統治時期,而經歷過大革命的法國社會對此毫無免疫能力。
伯克認為必須澄清自然權利和自然法的真正含義,以對立於平等主義和激進思想宣稱的每個人都具有的不可被剝脫的所謂「天賦權利」或「自然權利」。他寫道:「在由形形色色不同階層的公民組成的所有社會中,有些階層必然居於最上層。因此,那些平等主義者,只是改變和扭曲了事物天然的秩序」(頁83)。從伯克的這段話中,他與盧梭之間在理解「自然」觀念上的根本區別得到顯著呈現:與盧梭那種前文明的、田園牧歌式的幻覺般的自然觀念不同,伯克所理解的自然恰恰是在文明制度和傳統慣例之下才得以可能的自然而然的秩序與律法。與此自然觀念相應,伯克區分了簽訂契約、進入社會之前的權利與作為公民社會中的人的權利,並且否認人有行使政治權力的「自然權利」。他以文明人在受到侵犯時放棄直接自衛權而把對自己的裁判交給法庭的例子說明,「人不可能在享受非公民社會權利的同時還享受公民社會的權利。他放棄自主決定什麼是對他最重要之物的權利時,他會得到正義,這樣他就會確保獲得某些自由,基於對它全部的信任,他做出了放棄」(頁97)。同樣地,人們在投資的時候勿論付出多寡都具有相同的投資權利,然而在獲得投資收益的時候卻不可能根據抽象的平等原則來利益分配,因此對公民社會中的人而言,「每個人在國家管理中所應享有的權利、權威和範圍,並不是人在公民社會所擁有的直接的、原始的權利」(頁96)。總而言之,人們是因為傳統、身份、教育、財產和道德本性而獲得行使政治權力的資格。由此可見,文明的社會人的權利,絕不是啟蒙思想家以想像虛構出來的、絕對均等的、需時刻防備著可能遭受侵犯的「天賦權利」,相反,它必須位於文明制度和傳統慣例的管束之下,具體而有限度,卻能夠保障個人正當利益。如果說習俗和慣例就是公民社會的法律,那麼恰恰在彰顯了自然正義的人類法律中,上帝的自然法才得以為人類所認識。然而那些尚未在人類法律中呈現出來的自然法仍舊對人類隱而不顯,任何對這些部分的人為忖度都並非對上帝的虔敬與遵從。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標榜理性主義的啟蒙哲學家們試圖以僅僅通過人類抽象思辨能力來把握的哲學家的律法來等同甚至替代上帝的律法,不過是狂妄自大、招引災禍而已。他們鼓吹的「人權」要麼是妄想,要麼是謊言,要麼註定將在實踐過程中造成社會崩解。只有順從上帝的律法,遵循習俗與慣例,維護自然的等級與差異,承認人類有著理性以外的複雜多樣性,繼承傳統,仰賴成見,便宜行事,才能使人類社會走上一條平穩的、可延續的,避免人類個體或集體的愚蠢、彰顯人類總體智慧的發展路徑。
拉塞爾・柯克在《保守主義思想》中如此總結伯克的思想:「他的思想體系預先否定了功利主義、實證主義與實用主義,同時還抨擊了雅各賓主義。伯克的幾乎無以倫比的社會預見才能使他認識到,法國革命不是單純的政治鬥爭,也非啟蒙運動的頂峰,而是開啟了一個顛覆道德的進程,而且直到這一病症——也即反抗上帝護理導致的無序——自行耗盡其能量之後,社會才會復甦」。然而令人近乎絕望的是,自大革命到二十世纪,乃至二十一世紀即將進入二〇年代之際,這個顛覆道德的進程仍舊打著崇高、公義的旗幟,繼續恬不知恥地極力消耗著人類社會,並且在經歷了二十世紀的曲折與「解放」之後只變得更加有恃無恐。在伯克自己的時代,他已經面臨著文明社會遭遇滔天巨浪來襲而無能為力的困境:「伯克幾無可能阻擋他那個時代的這一趨勢:讓每個人都以自己的見識根據轉瞬即逝的環境和不完美的知識形成自己的觀點」。而到了二十一世紀,網絡科技與社交媒體則對上述進程的深遠開展推波助瀾……
參考書目
《法國大革命反思錄》,【英】艾德蒙·柏克著,馮麗譯, 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